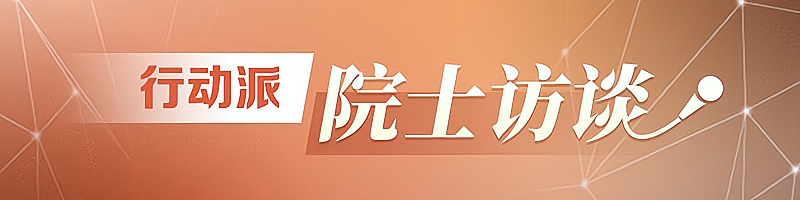
【编者按】
大众新闻客户端重磅推出“行动派·院士访谈”大型融媒报道栏目,邀请院士紧扣三中全会精神,结合山东实践,深度解析各领域高质量发展,从而汇聚各方智慧力量,一起来做“行动派”。本期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,古生物学家徐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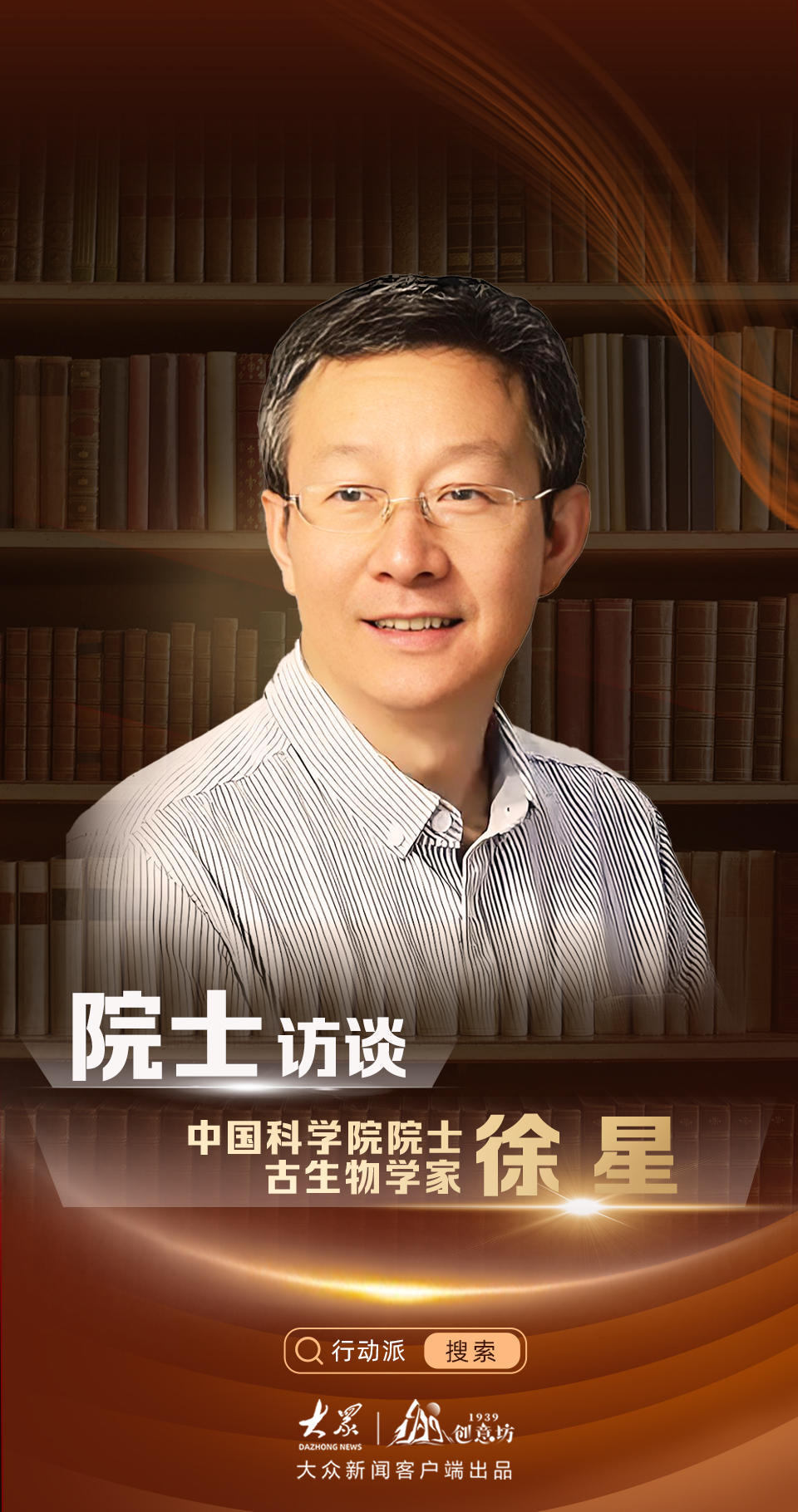
【院士档案】
徐星,古生物学家,主要从事中生代陆相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学研究。1969年7月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。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,1995和2002年分别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和博士学位。20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。
中国是目前全球恐龙化石发现最多的国家,截至2024年,徐星院士已发现并研究命名了80余种恐龙属种,占中国已命名恐龙总数的近三分之一,是全世界发现并命名恐龙属种最多的科学家。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恐龙院士”。
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人才强国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,健全新型举国体制,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。
——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

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。科技创新、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。如何培植科技发展的沃土,让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成为青少年探索科学的“启蒙导师”?如何激活文旅融合的区域经济新引擎?近日,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徐星接受大众新闻的专访。

大众新闻:山东有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,徐星院士多次来到这里进行科学考察、科研交流工作,近日再次来到天宇自然博物馆。这样一座县城里的博物馆有哪些地方吸引到您?
徐星院士:大家可能想象不到,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“藏”着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。人们常说,天宇自然博物馆是研究带羽毛的恐龙最重要的地方。这里有着大量的岩石标本,大量的矿物标本,当然更重要的是,还有大量的化石标本。这里收藏的带羽毛的恐龙化石,早期鸟类的化石,堪称世界第一,远远的超过世界上其他的博物馆。天宇自然博物馆兼具科研与科普价值,是自然爱好者的“宝藏地”。

大众新闻:中国恐龙研究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?
徐星院士:历经几代人的努力,目前中国恐龙研究相关的一些科研指标处于世界第一位。以赫氏近鸟龙为例,它是2009年我们命名的小型带羽毛的恐龙,其化石的发现,为研究恐龙向鸟类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关键证据。
很多学者认为,赫氏近鸟龙可能代表鸟类演化支系的早期分支成员。其生存年代约为1.6亿年前,较始祖鸟更早约1000万年。该这一物种不仅全身覆盖羽毛,且前肢已具备类似原始鸟类的翼状结构,形态特征高度契合学界对早期鸟类的理论预期。随着研究的深入,未来教科书中“鸟类起源”的经典案例,可能会从始祖鸟扩展至赫氏近鸟龙。
大众新闻: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提振消费工作放在首位,各地也都在聚力文旅的优供给。包括临沂平邑、费县以及潍坊诸城、烟台莱阳等在内的山东县域,不少都拥有恐龙化石资源。对县域恐龙主题文旅事业的发展,您有着怎样的思考?
徐星院士:在山东的诸城、莱阳,包括我们刚去的临沂费县,都有很好的恐龙化石资源。而恐龙不止受科学家们喜爱,也是大众文旅的重要资源。文旅是综合的,丰富多彩的,非简单的拍拍照片看看自然。
我们认为,现代文旅发展要跟科学普及紧密结合,所以也有了一个概念——科学普及和文旅事业的融合发展。恐龙则是很好的一个抓手,天宇自然博物馆作为山东第一座自然博物馆,便是很好的例证。

在过去,我们的文旅产业更偏向人文,但现在我们需要融入更多的科学元素。比如看见山川河流,需要去讲解山川河流背后的地学知识,包括岩石、河流、地貌是如何形成的。山东诸城恐龙涧有世界上单体最大的恐龙化石保存场地,诸城野外也保存了大量的恐龙化石,怎样让这些资源成为我们文旅事业发展的助推器,是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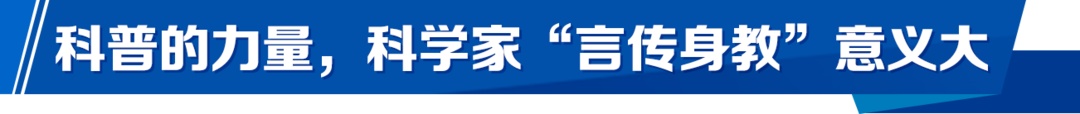
大众新闻:新修订的科普法明确,国家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。近年来,您一直热衷科普工作,科普文章《飞向蓝天的恐龙》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。为何如此热衷于科普工作?
徐星院士:我从事的是研究恐龙化石的古生物学专业,它是科学的分支,也是科普的载体。培植科技发展的黑土地,对于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,我们需要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,让青少年更多的关注科学、从事科学,我们国家的科技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进步。
科普就是要触及每一个公民。科学家和一线科研工作者做科普,言传身教的作用更大,可以引导孩子关注科学、关注自然。让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,也能让公众更快地了解科研进展,同时让孩子们了解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思维方式,更重要的是埋下一颗种子。

另外,科学科普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我国有灿烂的5000年文明,有灿烂的人文文化,但我们也需要培植更多的科学文化,使中华文明融入更多的科学元素,建立更加全面的文明体系,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。
大众新闻:在我们看来,古生物学家就像侦探一样,从破碎的骨骼、平平无奇的石头中,去还原亿万年前的生物行为,这对于平常人来说,简直难于登天。您是如何数十年维系这一份坚持的?
徐星院士:最初,我们只关注自己的研究,能不能发布科学论文,能不能做出科学贡献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,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,我们的研究会影响周围的人,影响整个社会。
我们的国家需要发展科技,需要培养年轻一代。通过我们的科学研究,赋予更多科学方面的培养,而在科学培养之后,又体现了科学的精神、科学家的精神。
古生物学不止是一项基础研究,也是对学科本身的推动,包含着对自然的认知,甚至哲学层面的认知。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融合的体系,比如之前提到的文旅产业的发展,在科普中融入科学的因素,促进古生物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与科普的融合。从普通的市民,到科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……都会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作用,我们的思想和见解,最终会融入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。

大众新闻:66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导致恐龙时代终结,而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第六次大灭绝,您能否为人类提出适用于现在地球生命系统的“生存指南”?
徐星院士:生物演化的研究中,有一个重要的方面,就是研究生物的灭绝。地球历史中的生物多样性一直在变化,有大量的物种出现,也有大量的物种消失,大规模的集群灭绝称作生物大灭绝。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66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,横行于地球的恐龙似乎一夜消失。
而我们人类就有可能处于这样的阶段,我们的环境看似非常友好,地球非常祥和,但公众不知道目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速率,有科学家推测我们已经接近这种大灭绝时期。
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现在的情况,也许我们的命运就会同恐龙一样,地球上不再有人类说话的舞台。无论是通过研究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、教育当代青年,还是普及公众认知,我们都需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,保护我们的家园。
大众新闻:您是古生物学专家。我们想通过您的视角,来思考一个问题——人工智能是否能超越人脑智能?我们该如何拥抱AI?
徐星院士:近几年来,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,势不可挡。在我收到的来信中,有许多青少年朋友对此非常迷茫,担心会影响未来就业。人脑能否被人工智能所替代,不同科学家持不同的态度,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对人脑提出了巨大的挑战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:国家的层面上,我们怎么样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?个人层面上,我们怎么拥抱人工智能的发展?
在我看来,首先影响到的是专业方向的选择,我的建议是先做一做调研,看一看未来,比如从就业的角度,哪些方向哪些行业可能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更小,再考虑未来的专业选择。其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也许大家都感受到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的工具,就像是当年的一些常用软件,如果不会使用人工智能,基本的能力就有可能受限。
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,我们都需要掌握一些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,帮助我们提高学习与工作效率。我们以前都擅长做题,给出答案,但这是不够的。对于我们的学生,对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来说,教育学生学会发现问题,提出问题,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是我们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思考的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大众新闻:对于偶尔迷茫又满怀憧憬的青年朋友,您有什么话想要分享?
徐星院士:我从小就喜欢很多东西,但到20多岁才发现古生物学是我真正擅长和喜欢的。认识自己、追逐梦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经历、一种体验,是培养一个人很重要的部分。
没有方向、没有专长,不是最关键的,重要的是在生活和学习中体会生活、体会学习,不停地去努力尝试,在过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和热情。
并非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轰轰烈烈的,但你在细微的事情中,会逐渐做出一些宏大的事情,或者做出一些激动的事情,也就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。
(大众新闻记者 卢鹏 王雅洁 刘玉凡 刘祯周 实习生 郭子绮 设计 杨雅晴 车婷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