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审查核实后,认为法院原审判决并无不当,对申请人作出了不支持监督决定。但办案并未止步于此,今年3月,通过检察院与法院合力协调,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,涉及四名股东、两家企业的商事纠纷得以圆满解决。” 日前,在浦东新区检察院召开的商事检察发布会上,一起关于追加、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的申请民事监督案作为典型案例之一发布。 不满民事判决,申请检察监督 2024年6月,民事与行政检察部门检察官受理了袁某等四人的监督申请,该四人同为S公司股东。 此前,因合同纠纷,K公司将S公司诉至法院,法院查明后判令S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K公司合同款100万元及违约金81.9万元。 因S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,K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,而法院通过穷尽财产调查措施,发现S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。于是,K公司请求判令追加尚未实缴出资的袁某等四名股东为被执行人,要求四人在各自应出资范围内对S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。经传唤,袁某四人及S公司均未到庭,法院依法缺席审理,于2023年11月17日判决支持K公司全部诉请。 袁某等四人不服生效民事判决,向法院申请再审。2024年6月,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。袁某等四人不服再审裁定,向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监督。 细致调查核实,维护司法公信 受理这起案件后,检察官听取了申请人的诉求。袁某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,存在适用法律错误,问题主要集中在四名股东是否应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。检察官认为:“要解决这个问题,还得从S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实缴情况入手。” S公司是一家设立于2015年的有限责任公司,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,股东出资实行认缴制,依据S公司章程,袁某等四名股东的出资期限为2045年7月3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相关规定,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设立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时,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需要考虑多种情形,其中,“公司股东是否已经完成实缴出资义务”是一个关键问题。 袁某表示: “原审判决之前,我们四名股东都已经以货币出资或者以知识产权、专利技术出资的形式完成了全部实缴出资,而且对出资及股权变更信息进行了公示,不应该再把我们追加为被执行人。” 为求证袁某等人这番说辞,检察官对S公司银行流水、审计报告、验资报告、知识产权出资证明等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审查,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核实申请人出资公示信息,调阅公司历年企业年报。 然而调查显示,袁某等四名股东并没有实缴出资到位,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。首先,除了个别年份,S公司选择不公示企业资产状况信息外,其他企业年报中各股东实缴出资数额均为0。其次,袁某等提供的由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、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确认的公司实收资本数额不一致,真实性存疑。另外,登记备案的S公司章程显示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,所以股东只能以货币出资,以知识产权等方式出资无效。 不支持监督申请之后,息诉止纷是关键 “经过细致地审查核实,原审判决并无不当,我们依法作出了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。这个案子看似告一段落了,但背后真正的矛盾还没有化解,检察履职仍在进行。”承办人说。结案后,检察官依然多次与袁某沟通,通过释法说理引导其正确看待法院生效判决,促成袁某等四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判决义务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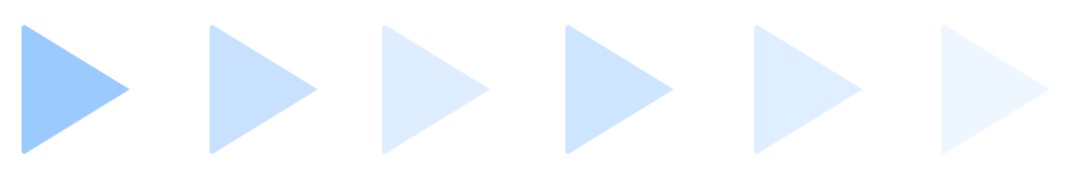


今年1月,四名股东、两家企业在法院协调下达成了和解协议。近日,被执行人袁某等人及S公司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了付款义务,这起商事纠纷得以圆满解决。 对于民事监督申请案件,检察机关是否支持监督申请,要以事实为依据,以法律为准绳,对调查核实后不支持监督申请的案件,还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,赢得当事方对司法的尊重与信任。承办检察官说:“直到双方握手言和这一刻,案件才算真正地画上句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