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中国文学走出去,似乎风头日健。今年2月,一批国内文坛大家亮相哈瓦那国际书展,使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,再次报以期盼和探究的目光。
这其中,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携他的作品《青鸟故事集》西班牙文版首次在古巴亮相,这是该书继法文版之后又一次在国外出版。
李敬泽将其视为一次珍贵的文学交流:“我的希望是中国文学能成为一只‘青鸟’,来自遥远的东方,翩然栖至地球的另一端,并将飞往世界更广阔的天空。”
►技术给我们“一切尽收眼底”的幻觉,但误解依然存在
作为文学批评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前主编,李敬泽一直置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中心。但同时,他似乎更倾心于写作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我现在还有力气寻找新的写作热情”。
《读无尽岁月》《小春秋》《致理想读者》《反游记》……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不急不缓地推出,他从没放弃对写作的探索。凭借2017年的两部作品《青鸟故事集》《咏而归》,他的作家身份更让人们熟识,也用文字吸引了更多的人。
《青鸟故事集》像是一本“志异录”,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在中国“迷路”的故事: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,莫名流落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,16世纪大明王朝的葡萄牙囚犯……李敬泽漫步茫茫史料中,把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放在一个写作熔炉里锻造。
而《咏而归》,从孔子、庄子等“巨人”开始,重现古人在精神上的风采和风姿,引领读者重新走进历史上最了不起的,但可能也是人们最不熟悉的文学时代。
李敬泽将这两部作品看作写给自己的两本“小书”,但他觉得,“小书”也是“大”的———“你能感受到人性和生命的宽阔。”
上观新闻:在刚刚结束的哈瓦那国际书展上,中国以主宾国的身份派出近130位代表参展。面对中国文学,古巴的读者有怎样反应?
李敬泽:中国文学吸引了相当多的当地读者,在中国图书销售区,古巴民众排起了长队,不少是专门前来的,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兴趣。中国在这个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所以,越来越多世界各国的读者对中国怀有好奇和认识的热情。
上观新闻:近年来,随着莫言摘得“诺贝尔文学奖”、曹文轩荣获“国际安徒生奖”、刘慈欣获得“雨果奖”,我们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。这是否意味着,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变得越来越顺畅了?
李敬泽: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,文学又没有长腿,怎么“走出去”呢?对一名欧美或拉美的读者来说,他不会说今天我要买一本中国文学的书,一定会说,我今天想买一本莫言的书,或者刘震云的书。
对他有效的是一个个中国作家,所以,中国文学走出去,实际上就是让中国那一个、两个、十几个乃至更多的作家走出去,让他们的人和作品一起被认识。当然,这条路还是很漫长的,比如在美国,出版的虚构类和诗歌作品中,只有不到1%是译作,而这1%里60%还是欧洲或加拿大的作品,可想而知,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。
上观新闻:这次带着您“走出去”的这本《青鸟故事集》,讲的却是中西交流间的误解?
 李敬泽:对,因为书中的各个故事都与误解有关,我也称它为“误解小史”。比如,《八声甘州》里明朝皇帝把利玛窦的自鸣钟视为新奇陈设,官僚们把地图当画一样装裱起来挂在厅堂,这是两种文化互为他者的误读;
李敬泽:对,因为书中的各个故事都与误解有关,我也称它为“误解小史”。比如,《八声甘州》里明朝皇帝把利玛窦的自鸣钟视为新奇陈设,官僚们把地图当画一样装裱起来挂在厅堂,这是两种文化互为他者的误读;
《飞鸟的谱系》则是翻译的“闹剧”集锦。当一场战争迫在眉睫时,道光皇帝所批阅的英国人发来的“最后通牒”,却因为华而不实的“改译”变成了请求中国皇帝主持申冤的“陈情状”;
还有知府、通事、印度水手和工匠之间交流的荒诞剧。工匠没有奉命翻译,而是借机向水手推销自己的店铺生意,然后胡诌些糊弄知府的回话,这一幕分明是把误解当理解的寓言。
上观新闻:您觉得,国外读者能从这些关于误解的中国历史故事中感受到什么?
李敬泽:误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,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之中,也不仅仅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。时至今日,世界各国对中国依然有着种种误解,我们也在误解着别人。
我觉得,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,误解可以说是命定的、一定存在的。为什么呢?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事:你如果和一个操不同语言的人对话,需要翻译,这里面就肯定存在误差,一百年前是这样,一百年后还是这样。
这样的误解能不能克服?有些是可以逐渐克服的,但有些误解要克服是非常非常难的,或者说不是你努力就能克服的。说白了,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间的交流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,哪怕同样是中国人、同样说汉语,也不能百分百地达成理解,这种理解甚至夫妻、父子、母女都常常做不到。
误解的产生也和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关。就拿文学来说,我们在和外国相关人士的接触中确实感受到,他们会因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,而对你的文学感兴趣。另一方面,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,你会感到一些媒体和评论者并不是真的把你的文学当作文学来看,而是只作政治解读,对作家的评价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。这里面既充满着误解和误读,也存在着偏见乃至敌意。
上观新闻:误读的普遍和易发生,是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交流的重要与艰巨?
李敬泽:为了尽量消除这种误解,我们确实要做出更持久的努力。文化交流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,没有什么捷径可走,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毅力。在交往的过程中,我们也要坚定文化自信,有一个积极的、坦然的、宽阔的心态,不必抱怨别人不理解我们,每种文化都是从自身的背景乃至利益出发去理解别人的。
虽然今天是一个“全球化”的时代,但是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误解未必就比嘉靖或乾隆时代更少。世界好像更开放了,技术给我们一切尽收眼底的幻觉。但其实误解依然存在着,只不过我们习以为常,失去警觉,意识不到了,长此以往,是很危险的。
在这个全球化时代,中国正在日益走进世界的中心,就像我最近去古巴、智利,中间在巴黎转机,一路上都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中国的存在,中国的“存在感”非常强,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性的中国。在这样的时代,如何作出努力,与不同文化、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达到尽可能接近于真的相互理解,并在这种理解中扩展我们的自我认识,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
►如果充满了不敬,在众声喧哗之后,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
熟识李敬泽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很“讲究”的人。他每天的衣着搭配都很精心———西装一定要修身,领带的色彩要和谐,还善于使用配饰。所以,他一站在那里,就会引人注目,用符号学的一个概念,叫“标出性”很强。
在李敬泽看来,对衣着的讲究其实藏着一个“敬”字。他的名字中有个“敬”,他觉得这个“敬”就是“面对任何事情,要有一种敬意,对他人对自己都要有一种敬意,庄敬自强,“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有这一份敬意,这是传统中好的那个东西”。
他的“敬”还体现在对工作的认真、对自己的认知上。即便是各种会议发言的时候,他也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和学者的识见;公开讲话时基本没拿过发言稿,但同时分寸感又很准确。他会让在场的各方都舒心,但又绝不会让人感觉到刻意。
确实,“敬”不仅是出门前要对镜整衣冠,更重要的是,对人有敬意,更要临事而敬。“就像一个鞋匠,对鞋取一个敬的态度,把鞋做好补好。没有这个,天天想着做大事,觉得做眼前那点事委屈你了,这个就真的有问题了。”
“我们这个时代,所多的、所重的都是‘敬’的反面,是不敬、粗率、轻浮、潦草等。过去的文人,他们的‘不敬’是有‘敬’做底子;而现在,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,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。”
上观新闻:您给人的普遍印象是绅士儒雅,但作家毕飞宇却形容您说,“这个人绝不像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温文尔雅,在精神上,他狂野,嚣张。”对于这样的说法,您认同吗?
李敬泽:人都是蛮复杂的,我现在坐在这里,就把能拿出来见人的一面摆在这里,但你放心,每个人都有不好拿出来见人的那一面。和我一起工作的人,都知道我脾气有些暴躁,还有人批评我傲慢。我经常照镜子,发现这个脸一吊,真是让人够受的,我这张脸确实不够亲和。但我觉得从总体来说,暴躁也是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,这是对于认真的固执。我经常讲一句话:人生何其短,坚决不凑合。
我从20岁开始工作,就是和作家打交道,我深知,投身到这个行当中,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写作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事情,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很难得到什么支持,别人也帮不上,只能自己面对压力。所以,作家内心都是高度纠结、紧张、脆弱的。我老是说要对作家好一点,他们真的是把最好的那部分放到了作品里。
上观新闻:您是文学批评家、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,这三种身份是如何在您身上协调,并彼此间相互促进的?
李敬泽:上世纪80年代以来,我们逐渐习惯于一个人单一的专业的身份,这实际上不是常态,你看中国传统不是这样的。比如说鲁迅,他是小说家、杂文家、研究古代小说史的学者,他还曾是教育部的官员、教授、社会活动家、中国现代美术的推动者,等等。现代史上很多作家,第一身份是革命者,更不用说古代了。
我自己从来也没有觉得同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以及作家、批评家是一件不协调的事。文人常发的牢骚是不屑于具体事务,觉得受委屈,案牍劳形、大材小用。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大材,同时我也觉得做事情其实也是在修行。
上观新闻:您曾提到,“敬”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,也是当今时代人们该有的品质。这也说明,社会上确实还存在着许多“不敬”与“粗糙”之处。
李敬泽:我不喜欢粗糙,我们也远没有精致到需要粗糙一下、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。同时,我相信,时间将会证明,任何人类成就都不是容易的,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容易,那不过是表明了我们的轻浮。
文学也一样,需要沉潜一点,安静一点,需要郑重其事,如果充满了不敬,在众声喧哗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?一个时代可能很热闹,但是热闹之后,留不下什么真正的果实,这是很正常的文化生态。社会上有很多喧嚣的存在,但真正从艺术上和创作上来讲,恐怕需要大作家、大艺术家来做。但同时,艺术家或者作家也许会从巨大的喧闹中获取力量,获取启示,甚至目睹一个新的可能性的出现。
文化是个大自然。什么叫大自然?就是野山上什么都有,可能有一棵很高的大树。你要是把草给拔了,把灌木砍了,等着大树出来,大树却出不来了,大树一定得在万木葱茏的地方长出来。
►回到强健充沛、元气淋漓的文化源头,把它变成自己的燃料和能源
李敬泽在文学圈更受关注的一个身份,是文学批评家。但按他的说法,写文学批评是被朋友、编辑“逼上梁山”的,“一开始偶尔写,一些朋友、一些编辑说写得好,纷纷约稿而且催债,然后就越写越多”。
他评论《废都》里的庄之蝶:“他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‘文人’:结交达官,掺和政事,诗酒酬唱,访僧问卜,就差开坛讲学了。”他写《花与舌头》:“黄惊涛恰恰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,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,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,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,它要舌灿莲花,要让天花乱坠。”他说莫言是一个超级动物,“小动物的细微触感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内,即使是小动物,在他笔下也像庞然大物”。
他的评论以“不骂人”著称,这些年发现并鼓励了很多文学新人,毕飞宇、阿乙、李娟、冯唐等都曾得益于他的评荐。“我常常想,一个作家就算写了一部不靠谱的书,能是多大的罪呢?值得你去痛加修理吗?”
如果硬让他说出一条年轻作家的普遍缺点,他指出:“面对当下时,很多写作者都‘漂’着,一个人在真空中没法发力,他需要立足点。解决办法也很简单:回到传统,传统给了作家发力的一面墙。”
上观新闻:很多青年作家说您是一位“理想的读者”。一个文学批评家在当代的文学现场能起到什么作用?
李敬泽:对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说,他必须是个学者,同时也是一个当今文化现状的参与者。
文学批评家的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个方面是经典化,把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、最好的作家辨认出来,并通过有力的阐释让大家能够了解;另一方面,在文学中,肯定有部分因素是模糊的、正在探索的,它们会逐步成型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强烈的自我意识,文学批评家要辨认、发现、肯定这些因素,帮助它们获得自我意识,帮助它们浮出水面。
在这个意义上,后面这个职责更难,因为辨认好的东西面对的是已知,而发现未成型的因素面对的是未知。我们在向前走,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儿。而也就因为是迷茫的,文学批评家才要帮助文学寻找到一个创新和前进的新的方向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上观新闻:从现在的年轻作家身上,能否看到中国文学的未来?
李敬泽: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,而值得注意的是,我们的新时期文学几乎是和改革开放同时萌生的。这40年里,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2018年的中国和1978年的中国,从最基本的日常经验、日常景观,到人们的观念、生活方式,说翻天覆地是一点也不夸张的,但是我们的文学呢?可以说文学的基本逻辑、基本观念,大致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确立下来的,一直持续到了现在,没怎么变。
我们现在读者心目中的重要作家,大部分都是上世纪80年代起来的,从文学意义上来讲,他们可以说是“立法者”,他们立的“法”一直管到了现在。但实际上呢,对于90后、00后来说,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,他们的背景和资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,所以我完全确信,随着新的一代的出现,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的压力。
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地辨认出他们谁是未来的莫言、余华或贾平凹,但是我相信会重新出现一批人,他们不仅仅年轻,还会为中国的文学带来新的观念和路径。这就是我对年轻作家的期待。
上观新闻:除了扶持新人之外,您也认为自己是“新锐作家”,但您的书大多是讲历史、讲传统的,传统与新锐之间有冲突吗?
李敬泽:完全不冲突。我们是现代人,但同时,骨子里、根本上,我们也并未走出传统。你可能一本经典也没读过,但你的人生态度、看问题的方法,甚至你的姿态和表情,都源自传统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需要有自觉,认识传统是为了自我认识,是为了活得更明白、更清楚。
很多人一谈传统就觉得,那么多书、那么多典籍,没文化看不懂啊。但传统不能仅仅是做学问的材料,也不是你成了钱锺书你才有资格谈传统,传统应该是活的,它有生机和活力,它所蕴藏的巨大的创造性资源,需要一代一代人、每个文化人从各自的层面、角度去体会、阐发、理解,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燃料和能源,支持我们去进行新的创造。几千年来,中国文学每每山重水复的时候,作家就要回到那强健充沛、元气淋漓的源头上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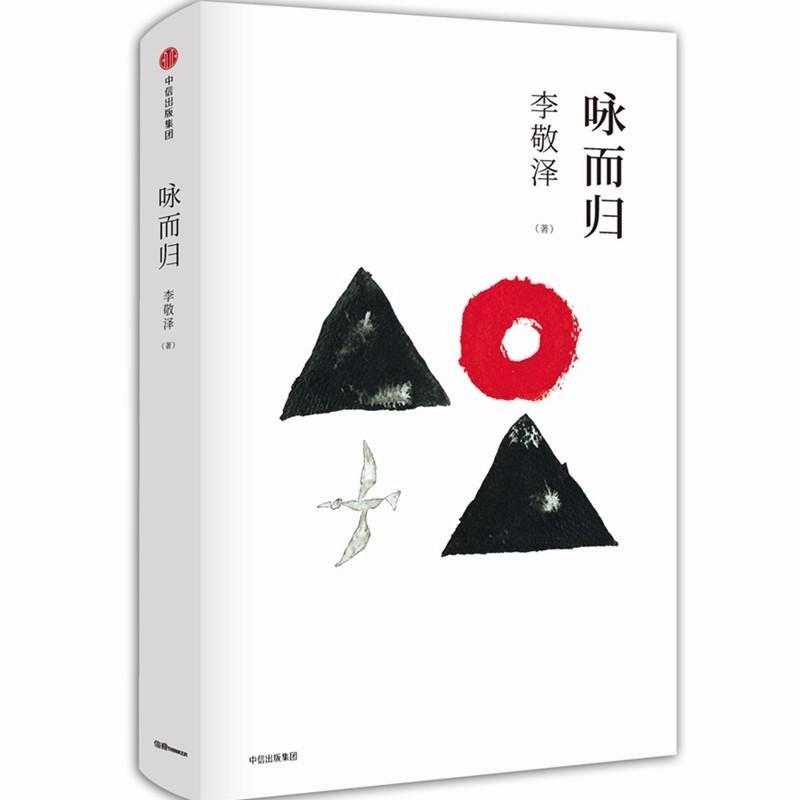 上观新闻:在作家和作品不断“走出去”的背景下,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,传统的重要性是否也更加突出了?
上观新闻:在作家和作品不断“走出去”的背景下,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,传统的重要性是否也更加突出了?
李敬泽:确实如此。中国文学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创作背景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很少有作家会想到写的书有中国读者也有外国读者,除了中文,还会被翻成多种语言。而现在的作家,至少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,他们的预想读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,因为读者不仅仅在中国,还在全世界。
所以,对于我们这代作家,如何立足于中国经验,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,同时,又如何面向世界并满怀自信,是全新的考验。我觉得对于这一点,中国的作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。
李敬泽
1964年生于天津。文学评论家、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。曾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,创办英文文学期刊《Pathlight》。出版文学评论专著及文集《颜色的名字》《读无尽岁月》《目光的政治》等,散文集《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》《河边的日子》《小春秋》等。
 我也说两句
我也说两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